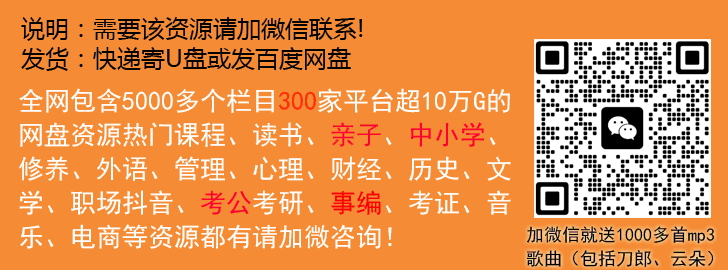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许立志
一
写作的烦恼伴随了我半生。
我的所谓写作,其本质并不神圣,无非是一个积累了各种心理问题无法排解的年轻人在无法与外界顺利沟通时拼了命涂抹一张纸罢了。期间又昏头昏脑的读了许多书,来不及消化,半懂不懂,误将别人的思想拿来装扮了自己。这样一来,与外界更无法沟通,涂抹得也就更凶了。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它结束于我进入社会之时。如若它不结束,我就要结束了。社会就是这样的存在。就像一本心理学著作所说:“如若不杀死以前的自己,现在的我就没法活下去。”(当然,作者想要表达的定然是正面的意思,毕竟过去的已经腐朽。)要么顺着自己的性子走去,要么顺着别人的性子走去。我选择了后者,紧接着听到以前的自己一声惨叫。他死了。
我的所谓写作,其本质并不神圣,无非是在已死与未死之间关于交替挣扎的点滴记录。对于活人来说,死只是一种伪命题,是一个没有旁观者的仪式,代表着旧的已经消亡,新的尚未成长。死是临界点,是质变的某种征兆,是琴弦受力断裂的一刹那。当这种仪式像模像样地举行后,作为人,或多或少是有些变化的。“啪”的一声,所有一切都断了。新生的我再也不会写了。
干嘛要顺着别人的性子走呢?我经常这样想。好像自己有权利去选择一样。其实,真相就像一场不公平的赌博,看上去有两张牌,其实只是一张牌在老千的手里换来换去。老实巴交的我横竖只有一条路可走——输。
个性,对我也是一种伪命题。
之所以丧失了写作的能力,无非是意识到以前所写的东西毫无价值罢了。它仅是某种毫无理性的情绪,某种杂乱无章的逻辑,甚至是人云亦云,只是藏得深了一些。在生存这个真命题前,昔日所学所思所想就像风化的石头,毫无用处,甚至还成了负累。总是惊异于别人,他们从来不考虑写作的问题,也不考虑生的问题死的问题,哎呀,他们才是正确的呀,平日的生存已经如此艰难,我要比别人花上好几倍的气力才能学会如何接受这些不成文的社会规则并且不感到恶心头晕,才能学会如何习惯毫无价值的忙碌并把忙碌看成是一种历练。我听到自己价值观的门轴在吱吱作响,内心的世界已经支离破碎,但他们才是正确的呀,务必笑容满面,不能将内心与现实变成冰与火,阴与阳,神与魔,我要撑住呀,我要改变呀,我不可以告诉别人有些苦痛会在我心里无限制地放大!
当务之急难道不是忘记写作吗?仔细一想,它实在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我必须找到恒定的足以指导我生活的准则,独处时,处世时,喝酒时,汇报工作时,接受批评时,撰写公文时,都不至于自我分裂。
但我很快就知道,这世界没有恒定的准则。我也不可能忘记写作。我只是在渐渐习惯和年岁增长中时刻警惕,放弃思考,试图装出常人的模样。和年轻时相比,只是多了一些自我保护的经验,我还是那个积累了很多心理问题无法排解的人,要想一边和这样的自己和平共处,一边能够应付这个社会,真是伤透脑筋。
二
我也做过关于写作的翩翩的梦,并为此拼过一阵子。
路线规划图是明确的,因为当上作家,既没有上司,又不用上班,高兴见谁就见谁(貌似村上春树说过这话?),不需要应付酒局,幸运的话版费还挺多,足以支撑整个家庭。这难道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这个写作梦的确也支撑了我好一阵。只不过写出来的文字极为干枯。于是某个自己又站出来说:“哎呀,写作可不能这么功利。写作可是灵魂干的活儿。背叛灵魂,你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另外一个自己就怒气冲冲说道:“老子哪里还管这么多,灵魂是个屁!”
总之,写作梦就这么不了了之。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半夜醒来时,就像睁开了黑暗的眼,思绪泛滥成灾,某个自己就像劝我吸毒一样让我披起衣服写点文字。哎呀,写吧写吧,反正已经不年轻了。
写作只能产生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写作的愉悦只是一种幻觉,它的本质就像某个病人中暑时给自己适当放点血。当然,还能有更粗鄙的比喻。它的交互作用如若没有读者就毫无意义。但写作又是这么自我的事儿。就像我年轻时那样,没头没脑地涂抹文字,完全不顾及他人。当然也有个别人能够读到,对于文字的解构,对于文字背后那个人的好奇,文本解读与真实意图之间的落差,这些虽然珍贵,但对于一个固执且没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只会产生虚荣的错觉。
这是多么不可靠的行当。
比写作更不靠谱的就是写作者本身。也就是我。我经常怀疑,所谓思维、灵魂、情感之类的异同,也许是身上的分泌物多一些少一些的缘故,就像喜欢一个人是因为血青氨和巴多氨分泌多了,我们之所以感知幸福,是因为头脑分泌了内啡肽。而激动不过是因为肾上腺素过多。所谓的思考兴许是身体和我们开的玩笑。所以当我们写作时,身体里的各类分泌物也异常忙碌,它们欺骗我们,让我们误以为自己构造了一个精神世界。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毕竟大脑运转也是神经元发电的结果,卡耐基曾说过,我们之所以像个常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非是比那些白痴多了小微量的碘元素。
在各类分泌物的操控下,写作者不过是傀儡罢了。写作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因为嘴巴难以表达,或者害怕表达,表达了也没人听,于是就写了起来。明着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含蓄。渐渐的,就连自己也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了。于是就想把文字写得美一些,更艺术一些。
我疑心写作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过程。但我也不想因此否定写作唯一的功用,毕竟某些时刻,它能够让我宣泄痛苦。而痛苦却是真实的,痛苦也是分泌物对外界的反应,痛苦久了会得胃溃疡。
三
聊一聊写作之外的事。
比如处世。
当某人露出胆怯与退缩的神色时,别人就会像闻到了腥臭的猫一样随时进攻过来。譬如酒局。不会喝酒害怕喝酒的人一定是最容易被灌醉的。他微弱的反抗在别人看来就像是无路可逃的老鼠在吱吱地叫。多么可怜。让人掀起欺负的欲望。
以此类推。世事大抵如此。
这样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允许你一个人活下去。你得绞尽脑汁和周边的人事周旋,你得想方设法完成工作和照顾家庭。你不能任性,亦不能随性。你必须读懂规则,趋同规则,善良和恶,在这些规则当中没有任何区别。利益是核心,其余是表象。不管你存在任何问题,只要一露怯,就会节节败退。
很有战争的味道。
偏偏我是个胆小的人。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恐惧。越明白生活的真相,恐惧就越浓厚。没有安全感。人人都会伤害你。瞅准你的弱点,给你狠狠地来一下子。能够应对的方法就是装作强硬。就好像不会喝酒的人虚张声势。和写作时的姿态相比,这个满脸恐惧的自己简直猥琐得可笑且可憎。但似乎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是个连日常生活都穷于应付的人。当然,这兴许是心理出了问题,比如有了恐惧症。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些问题。所有的时间似乎都被生活吞尽,骨头都不吐。
习惯于在生活中扮演恐惧且忙碌的人后,我总是不经意想到另外那些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伙伴们。他们肯定是存在的吧,就像野草一般廉价。他们和我一样混在工厂,混在学校,混在基层公务员队伍当中,机械地重复生存,并在生存的夹缝中寻找意义。我们无法解决内心与现实相互抵触的矛盾,很卑微很正常地活着,很坚强很谨慎地活着,就像一根根被拉满了弓的弦,或是一个个胀到极限的泡沫,痛苦得无以复加,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极为冷静,以至于谁也看不见。
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恐惧?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自然也是分泌物的结果。但也可以瞥见思想的沙化和漫天的谎言组成的规则,上面已经明明写着不允许我这样的人存在。不是现在不行,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行。除非我乔装打扮,改头换面,直到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又是可笑的赌博,又是伪命题)。
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不堪一击,在心理问题生活问题和思想问题面前早已丢盔弃甲,但在头脑当中大约已经生了不同于别人的种子。不过,就算这样,我(们)也不见得很有价值。某一天真的像针一样掉在地上,也许也只是轻轻一响,不会有人注意吧?
写于2014.11.22 凌晨
改于2014.12.3早晨

补:这篇文章写于去年,是为了纪念一位叫许立志的并不出名诗也未必写得极好的诗人。转眼又是一年即将过去,这印证了一句话:我只不过是变化过程中的一个节点,虽由过去的经验而蜕变,但过去的我已然消亡。所幸文字是真诚的,心灵是真诚的,即便是被别人所不屑的那一点点“消极”,亦是真诚的。以此纪念自己的过去。
王建平 补于2015年11月12日
作者简介:王建平,豆瓣作者,著有《请珍爱这样的自己》、《般若》、《众生之死》等作品。个人微博:http://weibo.com/wasu/
全网知识馆hupandaxue.cn,星光不问赶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