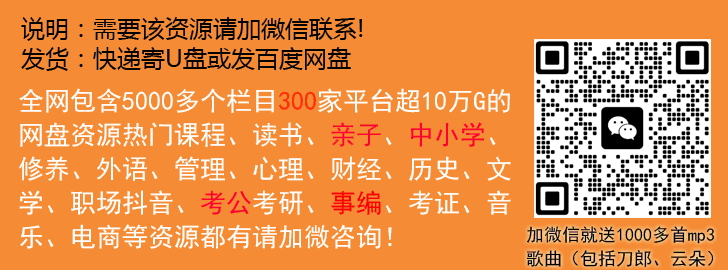文/稻田
在我的意识里,犹太人的面孔是飘忽和零碎的,唯一清晰完整的是,他们被纳粹当作囚犯拍摄的照片,呆滞而没有悲伤,恍惚却不见惊恐;此外就是聪明、富有、吝啬等的传说,但因为是传说,面孔就更是飘忽和零碎。
这是我接受妻子和女儿的撺掇,跨出国门的主要理由,我要试着去看看犹太人的面孔,哪怕多一点认识。

预定的计划终于到了实施的时候,先到了辛德勒工厂。工厂的原址已经做为记载那段历史的纪念馆,工厂地处郊区,显得荒凉和沉静,与沉静呼应的是默默等候参观的长队,都是欧美的面孔,我想,除了来此纪念前辈的后代,便是揣着像我一样的心思, 想端详一个民族的面孔吧?
灯光灰暗,梯道陡曲狭窄,与面孔最近的就是挂在墙壁的一幅幅黑白照片了。这些照片以前在书本和网络大多看到过,配注的文字倒是传递了更多的信息。

克拉科夫(波兰旧都)被占领之前,这间工厂是犹太人开的,被占领后,工厂自然开不下去了,精明的德国商人辛德勒趁机“买”了下来,利用廉价的犹太工人发战争财,工厂自然辛苦,却保全了性命,反倒令人神往,但保全并不能保证,纳粹党卫军时不时“照上级命令”到厂里来拉人去“处理”。做工就意味着活命。
于是,我看到了一群比照片清晰的面孔:一律惶恐地朝向厂主辛德勒,他们只能做这样一种期望,用他们的弱小,用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并且是将生命交给一位德国人(据说他还有德国间谍的身份)。

但利益和人性竟然在这位德国厂主的身上神奇地融合,后来几乎完全让位于人性了,他最后将本来用于盘剥的工厂办成了“避难所”,不计成本的保护一群无辜的生命,以至到后来,工厂无法维持,自己成为提着一只破皮箱,四处寄居的流浪者。
这个时候,我似乎看到了一张张深情的犹太人的面孔,他们在美国的大街上回望,在阿根廷的大海边遥望,在欧洲的某个地方伫望,朝着中东的一个方向,因为在以色列的一处公墓里,长眠着一位“异族人”—— 奥斯卡·辛德勒,一个值得生者和后代永远感恩和纪念的“朋友”。现在,到辛德勒纪念馆参观的人流中,一定有前来感恩和纪念的犹太工人的后代吧?

犹太民族是一个极具文化创造力的民族,千年无家园,千年遭驱赶,千年为客居,流落和流散之中,竟然靠讲故事的方式保持了民族的完整和文化的传承,其中感恩的文化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犹太人写满感恩的面孔,是在布拉格的一间中餐馆用餐时进一步清晰的。在与老板娘交谈时,我有意的将话题带到犹太人上来,“你能辨别犹太人吗?”“能,哪个国家的客人都能知道,头顶戴着一个小帽子的就是……”可能是看到了我迷茫的神色,她继续说道:“犹太人有一个特点,谁对他好,他会特别感激,一直记得,像中国人,二战时,上海人保护过他们,他们对中国人就特别好。”
我相信老板娘的说法,因为感恩是苦难的伴生,世代遭受了极度苦难的犹太民族,对每一个微笑和援手,都会极度敏感和感激的。
隔日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早心情便沉重起来,因为那里飘荡着数十万的犹太冤魂,似乎在清凉的空气里已夹杂了血水的腥味。
汽车要经过克拉科夫的犹太聚居区卡其米日,卡其米日是波兰国王的名字,国王将自己的名字赐给了首都(波兰旧都)边缘划出的这块区域,供犹太人居住和生活,有点“皇恩浩荡”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悲凉的安排,目的是要将这些异族人与本族人切割开来——在划定区域活动,以保证城市的“秩序”,以满足欧洲文化中的“排犹”心理。卡其米日在纳粹入侵时期几近空城,可以想象当时的荒寂和肃杀,即便是70余年后和平的今天,与游人鲜亮的克拉科夫中心城区相比,依然给人沉寂冷落感。不知是否为巧合或心理作用,在沉寂冷落的街巷看到的居民,面部的神情都显得沉抑。
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呢?被中东的邻居阿拉伯人驱赶,被欧亚的强权灭国,从祖居的耶路撒冷逃离, 流亡于欧洲大陆,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都十分突出,却在常人和恶人眼里都脱不去“异类”的面孔?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二战德国在波兰设置的多个集中营的合称,我到了其中辟为纪念馆的两个。一号集中营是波兰部队的军营改建的,除了围起的电网,营房的格局还很清楚,但已是关押囚犯的牢房。
空旷的营区,常可看见一队队的参观者从营房的窄门进出,一律的轻行寡言,无论男人和女人,无论老者和孩童,引导员沉重、低回的语调,更增加了气氛的压抑。队伍在暗窄的楼道里蠕行,突然响起孩子凄厉的哭声,孩子或许是被恐怖的遗迹惊吓,或许是被异常的气氛压迫得难受。父亲急忙将孩子带出 ,下楼消失在另一栋牢房的后面,但哭声仍从屋后传出,像一道射向长空的寒光,凄厉而坚硬,寒光的尾部痛苦地扭曲,我怔在窗口,想象着牢狱中犹太人胆颤悲伤的面孔。
遗迹就在一间间牢房里,如山的发辫,如山的饭盒,如山的鞋子,以及橱窗里囚犯被驱赶、杀戮的发黄的照片。
一抹红色抓住了我目光,我停下脚步。这是一只红色的鞋子,歪靠在鞋山的半腰,鞋面是绒布做的,这是一只女鞋,像是在家里穿的那种,虽也蒙上了灰尘,但在暗灰色的鞋堆背景中,依然显得十分的鲜艳。鞋的主人是一位优雅的贵妇或美丽的姑娘吗?主人被从家里赶出,挺着腰身走向军车时,知道是走向灭亡吗?为什么只是一只?是布展的人刻意将它摆在鞋山的表面,还是它托了主人的魂灵,执拗地从同胞的尸体里挤出,要人们看到它?我沉思其中,参观的队伍已经消失在走廊的拐角,我逼迫自己离开,红鞋主人高傲和冤屈的面孔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波兰的找寻是沉重和压抑的。去那个浪漫的城市布拉格吧。但我并无兴趣于蔡依林“误导”的那个“许愿池”和“布拉格之恋”。我知道,那里也有犹太人的面孔,作家卡夫卡在那里,犹太公墓也在那里,我可以走得更近,看得更清楚吗?

布拉格的繁华热闹远胜过克拉科夫,但更显出犹太先人的孤立悲苦。
难道是捷克人有意为之,还是命运的刻意安排?从巍峨辉煌的皇宫下来,迎面就遇到“黄金巷”,黄金巷并不是“黄金巷”,其实就是当时的工棚区,因为要就近为建造皇宫制造金器,住过一些卑躬屈漆,满脸烟色的金匠,便被意在增强古城吸引力的人们安了这个迷惑性的名字。
有意味的是,在卑躬屈漆的制金匠的身影当中,在烟火弥漫的炼金炉的烘烤当中,在一间站立转身都有困难的工棚当中,竟然住过一位犹太的文艺青年。工棚只有一人多高,我从唯一的一扇小窗望去,才发现工棚是建在深壑的边缘的,窗外绿树葱茏,深不可测。我尽力想象着这样一副画面:伴着金属的撞击声,一位秀气文弱的青年伏在破旧的桌前书写着,偶尔住笔望着窗外的绿树,眼里写满忧郁、愤怒和憧憬。这位青年就是死后才出名的犹太大作家,卡夫卡。
走下狭窄陡峭的坡道,我们向犹太公墓走去。公墓依然是犹太人聚居区,四周被高墙围着,生老病死都只能在高墙中,所以坟墓只好安在了屋前的空地里,生死相伴虽也亲和,但这是被逼迫的结果。
“小区”里有犹太人自己的教堂,规模虽然与墙外的天主教堂无法相比,但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公共设施,主的安慰和引导是他们生的支撑;空地里墓碑已成林,歪歪斜斜,挨挨挤挤,从数量判断,显然许多是后来陆续移入的,大概是孤处荒野的魂灵寂寞,或是后人担心他们孤单,将他们带回“家中”吧。

我沿着墓地的小路一圈圈的慢行,发现围墙上也有墓碑,密密麻麻,有的整面墙壁都排列着逝者的姓名,证明了人为的猜测。但所回之家真是家吗?这里其实是犹太人的软禁地呀!
唯独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塞满墓碑和墙壁缝隙的白色纸条,这些一定是犹太的后代塞入的,里面也一定写着给亡者的话语,我无法知晓写的是什么,但我分明看到了一张张鲜活和坚毅的面孔,在游人如织之中,在世事更迭之中,在风云变幻之中,犹太文化的血脉奔流不息!

从欧洲回国不久,看到新华网9月29日的一则报道,有以色列政坛“常青树”之称的以色列前总统希蒙·佩雷斯28日去世,终年93岁。

因为怀有犹太情结,我特别端详起消息配发的佩雷斯的照片,又想起前一位以色列总统拉宾的面孔。
两张面孔都布满皱纹,眼睛里都透出忧郁和坚毅。这就是我想找寻的犹太人的面孔吗?忧郁和坚毅,因为苦难而忧郁,因为要挣脱民族记忆里的忧郁而坚毅,因为居安思危而忧郁、坚毅,这或符合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命运和心理历程吧!
作者稻田主张用接地气的语言和形式,与大家分享“真事、真情、真感悟”。作品:《此为异客总多情》《执手束河》《魂念北屋》《故乡拾碎》《南去的列车——鹰厦铁路首行纪》《何处是乡愁》等。
星光不问记:我喜欢的犹太人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奥本海默、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沃伦·巴菲特、冯.诺伊曼、毕加索、卓别林、维特根斯坦等。
全网知识馆hupandaxue.cn,星光不问赶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