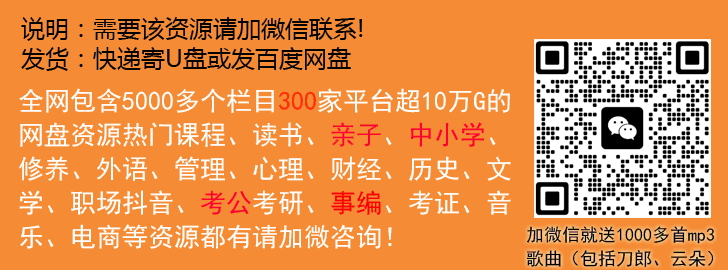“我在岛屿上观看着日出日落,潮来潮去,花开花落,观看着星辰的移转,观看着生命的来去和变迁。”——蒋勋
独白
选自:《岛屿独白》 作者:蒋勋
我坐在窗前,等待天光暗下来。我想,随着光的逐渐降暗,我的视觉也便要逐渐丧失辨认的能力了。但是,似乎这样的想法并不正确。视觉中有更多的部分与心事有关。可能是记忆、期待、渴望、恐惧这些东西吧。
如果能够去体验天生盲人的视觉,或许可以真正分辨“视觉”与“视觉记忆”之间的差别。但是,我已无能为力了。我闭起眼睛之后,我的“视觉”被众多的心事充满。仿佛如潮汐的泪水,逐渐沁渗在每一片极度黑暗的球体的边缘。这是一种视觉吗?或者,仅仅是我视觉的沮丧。
我的眼前,花不可辨认了,路不可辨认了,山,也不可辨认了。然而,我知道,那不只是因为光线降暗的缘故。是我坐在窗前,等待每一样事物逐一消逝的心境;花的萎败,路被风沙掩埋,山的倾颓崩解。在近于海洋的啸叫中,我们凝视着那一一崩塌毁灭的城市、帝国、伟人的纪念像……
在一个可敬的朋友出走之后,我刻意训练自己降暗视觉的光度。我想用晦暗的光看我居住的城市,仿佛在冥修中看见诸多幻影。(一般人都以为那如同魑魅魍魉,其实不然,幻影也可以是非常华美的)幻影之于现实,并没有很清楚的差异。我们大都必然陷入幻影之中。是因为它几乎就是一种现实。嗜食毒品者在幻影中感觉着一种真实;嗜杀者在杀戮中感觉着一种真实;啃夺权力者在胜利中感觉着一种真实;嗜欲爱者在欲爱的幻影中感觉着一种真实。
为什么我要说那是“幻影”?毒瘾中沁入骨髓的快感,嗜杀中屠灭生命的快感,权力的争夺,财富的占有,爱欲的生死纠缠,在我居住的城市,即使我调暗了视觉的光度,我依然看到这诸多的现实,如此真实,历历在目,对我的“幻影”说嗤之以鼻。
报刊上今天以小小的一个角落登载了你出走的消息。我因此独自坐在窗前,静听着黄昏潮汐在每一片沙地中的沁渗。有一种嗦嗦的声音,很轻很轻地渗透在沙与沙的空隙,好像要使每一个空虚的沙隙缝都涌进充满入夜前暗黑的流水。
沙隙间暗黑的水流,可能是一种独白,一种失去了对话功能的独白。(但不要误会,绝不是丧失了思维的喃喃呓语)独白,也许是真正更纯粹的思维。在一整个城市要求着“对话”的同时,我猜测,你的出走,竟是为了保有最后独白的权力吗?
在某一个意义上,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写小说者)是没有读者的。一个绘画者、一个演员、一个舞者,可以没有观众。一个歌手、一个奏演乐器者,可以没有听众。
我看到一个老年的舞者,在舞台上拿起椅子,旋转、移动、凝视。他在和观众对话吗?不,他只是在舞蹈中独白。
在修行的冥想中,诸多的幻影来来去去,盘膝端坐着,在闭目凝神中一一断绝了与人对话的杂念。
每一柱水中倒映的灯光,都是一种独白。它们如此真实,水中之花,镜中之月,指证它们是“幻影”,也许只是我们对现实的心虚吧。
如果你是水中之花,你大约会从水中抬头仰视那岸上的真相;如果你是镜中之月,你也会从明镜煌煌的亮光中抬头仰望那天空中一样煌煌的明月,发出啧啧的赞叹吧。
那么,你的出走,究竟是一种真相,还是一种幻影?或者说,你代替我出走了。
我留在现实之中,你替代我出走到幻影的世界。当你笑吟吟从水面向上仰视的时刻,我必须微笑着告诉你岸上的一切,包括阳光的灿烂,风声,以及我在风声中的轻轻摇曳。
据说,记忆中所有前世的种种,都只是今生的独白,因此,宿命中我必然坐在此时的窗前,等待天光降暗、降暗。
独白
好奇怪,忽然想起十九年前那个老年的舞者。他叫摩斯·肯宁汉(Merce Cunningham)吗?那年他有七十多岁了吗?应该是“国家剧院”,年轻舞者都表演完了,观众以为结束了,可以走到爱国东路上,坐“捷运”回家睡觉。然而在掌声之后,他走出舞台,沉默看着舞台中央一把椅子。单手提起椅子,旋转。手和椅子旋转,身体也旋转。椅子慢慢仿佛长在他身上,好像他老年肢体的一部分,沉重,向下坠落,但也有努力向上对抗坠落的意志。他不断旋转,有时快,有时慢,像云在风里没有坚持的速度。那是我看到的最后的摩斯·肯宁汉,好优雅的老年舞者,好安静的一把椅子,在上个世纪末喧嚣着各种表演的舞台,我在失忆中却留着这么清晰的一个画面。那个要出走到缅甸寺庙去的孤独者还是回来了,我想他忘不掉他眷爱的肉体,像我一样。
宿命
选自:《岛屿独白》 作者:蒋勋
我们用各种方式去探测未来,也许,在未来越混沌暧昧不明的时刻,我们越盼望着依靠一点点神秘的暗示,用来探测未来可能的线索。
我们手掌上就有一些似乎可以阅读的线条;人类从久远的古代开始,就在这些线条中阅读着未来的命运的种种,关于爱情、事业,关于吉或凶的一切可能。
手纹的阅读是极其困难的,据说,最好的命相家都无法准确地解读自己的手纹。
古代许多为帝王阅读命运的命相者多半是盲人。他们其实在视觉上是不可能阅读人的面相或手纹的。“命相的领域,一切的阅读都只是个误导,因为——”那位命相家在临终时这样交代将要承其衣钵的弟子说:“命相的终极并无暗示的线索,也没有解读的可能:命相的领域不能依靠世俗现实的逻辑,逻辑的理则推论越强,越远离测知命相的本质。”
据说,这名命相绝学宗师,便在临终前,亲手刺瞎了将承其衣钵的弟子的双眼。弟子恭敬承受命运,在鲜血迸溅前默默流下最后两行清泪。他从此再也不会流泪了,现世的种种景象在他的视觉中全部熄灭,是的,熄灭,就像照明的灯火熄灭,一切物象也随之隐没入无底洞的黑暗。
但是,他因此开始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命运的终极,看到变成婴儿流转于另一个人身体之中的师父,手中握着一柄尖锐的锥子,号啕啼哭,仿佛他已一一锥刺了自己的前生。
我们偶然感觉到的身体上无缘由的痛吧,我们偶然感觉到心中一阵不寒而栗的悸动,我们偶然盈满泪水的眼睛;不可解、不可知的种种,因为这些,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岛屿相遇,相爱或彼此憎恨,那双被椎刺后如黑洞般阒黑幽静的眼睛,都一一探测到了,他也只偶尔说一两句不相干的话,对一般人而言,是完全不可解的。
眼神犀利的人其实反而是看不到任何未来的。
岛屿一向热衷于探知未来,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吉凶。在一个新的年度将要来临之前,人们更蜂拥至庙宇或各个命相的所在,祈求神的祝福与暗示,依凭这渺茫幽微的暗示,做下一个年度生命的预算。
但是他并没有走向庙宇。他似乎知道庙宇已少了神的驻足。
他坐在电脑桌前,凝视着荧光幕的变化。
他尝试设计了一种软件,把人诞生的年、月、日和地点,四种因素输入,然后他就静坐着,等候显示板上慢慢找到那一个确定的时空。
我们在完全空白的领域里找到了一个小点。这个点,既不占有时间,也不占有空间。但是,那个点,就是我们诞生时存在的最初的时间与空间。
“命相里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个点的寻找。”他这样喃喃地自语着,他的明澈慧智的眼睛定定地凝视着显示板。
然后,一刹那间,围绕着那小小的一颗红点,四周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蓝色的小点,大大小小如星辰般密聚向那孤独的红点。
他阅读着那些小点排列的形状位置,“冥王星。”他以极科学的方式找到天空星聚的各种可能,也试图找到那些密聚的星和一个孤独的红点之间神秘的关联。
他所向往与深爱的一些小点移向星盘的某些角落,“魔羯,射手,水瓶,天秤——”他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起来,他知道星辰的聚散竟是因为它们内在的一种宿世的深情,“所谓宿命吧——”他这样喟叹着,“所谓命相的终极,不过是宿世以来深情的牵连不断而已。”他又看到一群蓝色星群的小点移向那一点点孤独的红色。
独白
所以,我应该更紧地拥抱你吗?只是因为无垠空间里那些星辰间宿命的记忆。
没有比紧紧地拥抱更使人陷入彻底寂寞的,我孤独的时刻,彻底孤独的时刻,才有了绝对的自由。
如同今夜天空的星群,如此密密地聚集在一起。
但是你知道它们彼此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吗?
人类从来未曾真正测知过宇宙的辽阔,到底有多么广阔?
庄子好像发过类似的询问,然而他的询问被后来头脑迂腐的注解者用尺寸限制住了,失去了无边无际的想象。
不能大胆走进混沌与荒谬,无法测知宇宙真相,也无法知道时间与空间真实的状态。
人类依靠理智去测量宇宙,却误入歧途,越走越远,也越和真理偏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宇宙的密码其实隐藏在庄子的“逍遥游”里,孤独而又自由,你刚觉得他是鱼,他已经是飞在九天之上的大鹏鸟了。“呵!呵!”仰望星空,就听到孤独者一声一声像叹息一般苍凉的笑声。
全网知识馆hupandaxue.cn,星光不问赶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