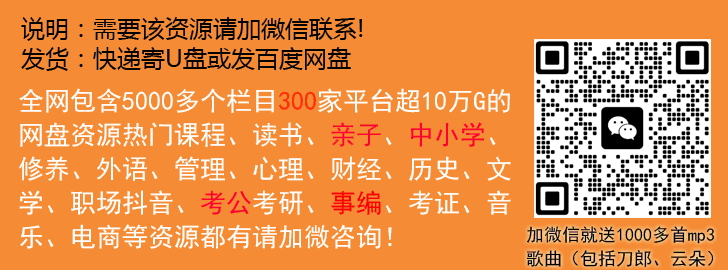文/邹近夫
到了中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破红尘,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故事大可以说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小可以说到与邻居阳关家争夺屋丈,常常是一寸的地儿,闹得不可开交。我以为是老死不相往来,但逢年过节,他俩却又坐到一起,有阳光的午后,就摇着扇子说从前,下雪的傍晚,就围着火炉迷迷糊糊地睡了。有时候还要我亲自登门去喊,父亲愣上老半天,才睁开眼睛,意犹未尽似地背着双手跟我回家。
往后余生,他谈起的便是陈年旧事,像英勇献身的战士一样,显得慷慨激昂,可一旦提到我,他就像喝得烂醉的人,眼里憋满了沧桑。事实上,谁也没法理解他的意图,也都没法忘记他曾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掀起的风浪。
1
1990年春,蓝白相间的大字,画遍了大街小巷,连不识字的文盲周老四,也知道那上面写得是什么东西。父亲虽身为村委书记,但在“不孝有三,无后乃大”的社会环境中耳濡目染了三十年,所以他宁愿冒着超生的风险丢掉官职,也要个儿子。那时,凡有此心者大都噤若寒蝉,母亲怀孕后,父亲主动递交了情况说明,一开始村里同辈人都劝他莫要做违法的事,可父亲偏偏一意孤行。村里只好革去父亲职务,还没收了家里攒了好几年的粮库。
父亲见到粮仓一空,就像一个输得精光的赌棍,一下子流出了眼泪。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春天,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见他流泪。这个曾让我引以为豪的男人,忽然蜷曲着身,倚在门边,像一只蝉儿留下的弃茧,风一吹就可能掉到地上。
我那时已懂点事了,为了不打搅到父亲,只是抓着母亲的衣角,默不作声地跟着她去山里捡菜叶。我知道他在为今后发愁,也知道他痛苦绝望,但我一点没看出他有后悔的意思。憎恨吗?只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苦,从鼻根一直涩到心底里去了。后来的日子里,我从不去看父亲的眼睛,因为那里没有我想要的依恋,但每当母亲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时,我总能从她眼眸中感到一阵心悸。
由于父亲书念得不少,虽不为官,但也常常帮着村里撰写文书报告。春耕生产样样在行,一到寒冬,还做起了蜂窝煤的生意。不到一年,家境渐渐有了起色。这期间,当然离不开他不辞辛劳的付出和日复一日的汗水。这都是很好很好的回忆,我偏偏不喜欢。只是因为二妹生下来的那一刻,父亲像站在风中一样,摇摇晃晃。我真不明白父亲的国度里除了传宗接代,还有什么?初冬的暖阳照在脸上,只觉得眼角冰冰凉凉。这天傍晚,我走向一望无尽的草坡,才发现我的全部心伤,不过是天边的晚霞,世间还有什么美得过它呢?可是我在夜幕降临前,迷路了。
当我大胆地迈向草坡寻找家时,黑夜来得太快。我抱着双膝,坐在草地上,看白杨一点一滴地隐进黑幕里,又渐渐地退出色来,尔后慢慢地向我靠拢。等到这一切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恐惧,把我吓哭了。一直以为父亲的国度里根本没有我,但这一天,看见一束电光射向我片刻,想也没想就奔过去扑入他怀里。我抬头看见那张黝黑沧桑的脸上浮出了笑容。从那以后,父亲像洗心革面一样重新投入生活。尽管我知道他在等待,等待一个可以让他托付终生的男儿,而且不久后他又会萌发生育的希望,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我曾走近过他的国度边缘。
2
1992年12月,寒冬的雪飘了一地又一地,连门槛石阶上都结了冰,我带着两岁大的妹妹走进雪地,远近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湮没了这儿的贫穷和落魄。一切都很美,美得像梦一样洁白无瑕。我把妹妹立在一株银杏下,在她眼前滚了个小雪人,妹妹的声音在空旷的雪原里像驼铃一样好听。只是不远处时常传来炮响声,震动了我的梦。我抱着妹妹站在雪人边,看一群男孩在地里相拥打滚,看见他们的鼻涕把引线浸湿,看了好久。我知道那是男孩子才有权力玩的东西,也从不敢向父亲提起,哪怕他把花炮递到我手里,比起诱人的烟花,我更愿意听到他的赞美。
父亲也许知道小孩子都爱烟花,也许知道不能灭杀一个孩子的天性吧!
那天他从裹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棉袄里掏出一盒烟花给我,一时间我不知该伸出哪一只手去接受父亲的爱。一旁的妹妹踮起脚尖打翻了父亲手中的烟花,我急忙蹲下身,也许是因为寒冷,指尖竟忍不住颤抖起来。父亲点燃烟头,蹲下身递给我,还嘱咐我小心。他转身时,青烟飞入我的眼睛,熏得我泪流满面。那一刻起,我所有的不甘和抱怨似乎都没有了,像大雪覆盖下的土壤,永远不会显露出来。
硝烟味闻起来让人精神振奋,从正午到黄昏,像放了个鞭炮一样,烟一散就没了。
我抱起妹妹告别那一地纸屑,再望向远处,一只不知时节的小麻雀惊碎了树枝上的积雪。我看见父母站在门口,背后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幽暗,我不敢去看父亲眼眸,因为那里有我一无所知的命运。他俩见到我和妹妹,便又像雪原一样寂静无声了。母亲自然是拗不过父亲的,可能她也觉得十分惭愧,连吩咐我做事都是小声小气,深怕惊吓了世界,而父亲好似把所有的遗憾统统留在了那个黑云密布的草坡,所以他可以放下重重顾虑。我第一次恨妹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如果是这样,那么家里就不会再面临危机重重的局面。还记得她出生时,我是多么开心啊!因为她违背了父亲愿望,并非男孩,而我万万没想到父亲依然有所希求。如果我提前知道这些,那么我会日夜期盼妹妹是个男孩。
3
第二年春天刚过,母亲便被送去了偏远的蔡山。这种动向被明眼人看穿,一时间流言铺天盖地,新任村委书记带队抄了家,但也不是没留有余地,农具,板凳、桌椅、衣柜和床,都分别留下一个,而我就坐在一只被不小心踩烂的菜篮里,望着他们进进出出地把所有熟悉的物件抬到门前的空地,一一点数,记好帐薄,然后用板车拖走。
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地下过之后,我轻悄悄地钻出篮子,像母亲一样,带着妹妹默不作声地提着镰刀去山里捡过冬菜。我不知道父亲为何放着好好的官不当,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宁愿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非得要一个男儿。但有一瞬间,我好似看到了多年后的自己,为了生育男儿而愧对世人。这个春天过得像一个秋天,青草都不曾发芽。也是这一年,虽然我没有去学校报到,可我日夜向往那飘着油墨香味儿的书本。
当一丛丛枯萎的冬茅草露出了枝叶,那些没有在冬天前散尽的茅絮,在阳光下二度展开,像飞雪一样倒映在初春的霞光里。我最喜欢把它们来握住,然后轻轻吹一口气,看它们飞走。妹妹问我,为什么吹走,它们要飞到哪里?我知道她还是个孩子,所以不会跟她说出我的梦。有一天夜里,妹妹忽然大哭,我心里一难过,就翻身起床,站在离她很远的地方,一动不动,等到她精疲力竭地睡下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全部坚强,不过是两行热泪。没过多久,得知家中境况的母亲从蔡山回来,一下子坐到门槛上,两眼婆娑地望着一贫如洗的家,半天没说话。可父亲倒不像三年前那样,反而精力更加旺盛,他好像能未卜先知,认定接下来的新生必是他的梦一样,还莫名其妙地开始借钱,向以前的战友,向不曾联系的亲戚,甘受冷落和蔑视,终于在冬天来临前建起了这里的第一座红砖房。
1994年2月的白城,寒气逼人,结了冰的原野上没见雪飘过,只有晶莹剔透的冰棱,悬在树枝上摇摇晃晃。3月初,一声啼哭,几乎揪碎了所有人的心,妹妹也不知为何紧张起来,也许他从没见过父亲那么严肃吧!
你等待过初春的朝阳吗?当雾霭散去,那芒草上的一滴露珠,可以镜像整个清晨,但这片细腻的风景不是爱恋,而是自然生命的无限猜想。
4
父亲的国里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男儿,正是那个皮肤皱得跟个糟老头似的小鬼,但我却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忙里忙外地端水洗尿布,还把整个屋子都扫了一遍。说不上是失落,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疑问消失不见了。我注视着父亲的眼眸,妄图知道这一刻的全部秘密,可那好似无需解答的事实,生活真相本该如此。
从此岁月好像染了色的布条,在青天白云下缤纷烂漫。
这一年,我再次走进学校,辽阔的草坪上依旧留着我曾经奔跑过的身影。因为年少所以选择风雨,我断然跳级,情愿面对种种考验,如此才不会落后同龄人。可往往是一地枯得发黑的梧桐叶,使我骤然想起从前父亲背我开学情景。那时我只消崴一下脚,父亲便会将我抱起,或者咳嗽一声,他便会把我包进大衣里头。在那双比天还大的手掌里,我曾闭着眼睛无需去看眼前的路究竟通往何方。因为在父亲的国里,我不会迷路,也不会丢失。
暮春的黄昏下,一丝青烟拖着淡淡的哀愁,漂浮在山头,时隐时现。我关上所有的窗,抱着课本睡到傍晚才离开学校。直至白城河,望见红得亮眼的红砖房,不由得徘徊了很久。我希望黑夜来临,然后看见一束光,但又害怕黑夜降临,会看见一地仓皇。
我知道自己是姊妹中最大的一个,所以不敢打赌父母会在天黑前寻找到我。回家后我像往常一样,将弟弟放进摇篮,一边洗衣服,一边看着他,他傻傻地向我笑,妹妹则在一旁用石子划着圆圈。可我感到头昏眼花,不幸倒下了。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脚步声,醒来后感到一身清冷,手背上还吊着针管。一种前所未有的寂静,是夜风拂动窗棂的响动,使我害怕的是父亲惆怅地将眼神投向我的刹那。生病给家里带来很大损失吧!我也知道这家伙怪要钱的。从此以后,我得学会保护自己,不受风寒。可谁会知道,未来的路那么长,弯路又那么多,我依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
5
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学校举行夏耘活动。那是一个刚到学校还没一个月的老师带来的游戏,他教我们两人一组,分别把腿绑上,然后跑步比赛。我向来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可这次,我那小组得了倒数第一。我气冲冲地表示,要来场单人比赛,但他说,人生一场,哪能没有同伴。
那是个没有余晖的傍晚,天色灰到了眼前。尽管有一种失落感缠绕着我,但瞥见老师那清澈的眼眸时,我一时明白了这些年的一意孤行,原来是无济于事的反抗。我渐渐懂得了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另一个人,他可以是亲人,可以是同学,也可以是朋友。这一天,我牵着妹妹的手走过白城河边,折断一支芦苇,把来路不明的哀愁全部丢进了水里。可是妹妹并没有问我为什么?也许她到了我曾经的那个年龄,还许下了一样的梦。
也是这一天,父亲作为抗战老兵从县城参会回来,他像一个来不及转舵的水手,一刹间翻进了波涛汹涌的往事里。不过从那以后,三弟的地位一下子一落千丈,我和妹妹受宠若惊。父亲变了个人似的,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我和妹妹。
适逢这一年,邻居阳关也开始筹建新房,可他的地头儿只有那么点大小,家中却有五个儿子,所以想法设法扩大房屋面积。这可能越过两家之间的分界线,遮挡阳光不说,还挡住了风水。他俩先是商量了一阵,在意见上没有达成统一,演变成吵闹的局面。最后大动干戈,搏斗中,父亲打折了阳关的左手,从此结下恩怨。在他们眼里,同样是男儿才可以保家卫国,再不济也能做根顶梁柱,可征战沙场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他俩一直理解的概念,冥冥之中发生了彻底性的转变。只不过父亲依然坚信有备无患,及至岁月渐渐地荡平了那段峥嵘,他才想起要和邻居争夺一寸土地。后来乡村干部出面,提议阳关从下往上建,这一语惊醒梦中人似的,让他喜不自胜。但两家之间的祸端业已酿成了。
三弟十岁那年暮春,小灵通覆盖了全国各地,父亲在堂屋里做起了通信行业,还张罗了酒席,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则把自己从县城学到的游戏带给全村,我同小伙伴们讲奥运会,还教他们跨栏,投掷铅球。意外发生了,在百米跨栏间,弟弟把邻居阳关家的四阿让推出了五米开外,一条黑色的血迹使我头皮发麻,我看见四阿让痛苦的叫着。不一会儿,爸爸撒下酒席,抱着他去了医院,那天的夕阳当真像躺在血泊里一样,令人心惊肉跳。
当我见四阿让的半个胳膊包扎着纱布,同父亲回来时,我知道大事不妙,也知道这不全是弟弟的过错,于是默不作声地等待一场狂风暴雨,弟弟则躲到我的臂弯里。可是父亲并没有责怪我们,而是转身从房间里掏出一只盒子,里边是一把五四手枪和锈迹斑驳的三等军工徽章,父亲还将一沓钱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我这才知道盒子里一直装着的是父亲一生的荣誉,我也只见过那一次。
无人的门前,不一会儿便挤满了人。阳关闻讯后忽然发出高叫的声音,似乎要拼命,还直呼父亲的名字,说要交出我才罢休,说那是一把没有子弹的手枪。黑幕完全降临了,全村都忘了开灯一样,四周是黑压压的一片,只有零星半点的烟头还亮着点红光。父亲自知理亏,所以从头至尾没有说一句话,只当阳关一步跨入家门的时候,父亲才迅速地站起身,立在堂屋正中间,和他对视。
有那么一两秒钟,我想走上去道歉,但这显然不会使一头发疯的野兽息怒。那天,阳关一没有选择钱,二没有拿枪,而是和父亲搏斗。他俩并肩走向了原野,走到那个我曾抱着妹妹看烟花的地方。我看见两个男人,在青黑的天空下,大打出手,始料未及的是这次搏斗让父亲的一条腿留下终身残疾。我永远忘不了阳关扶着父亲走进堂屋的样子,凶狠中带着坚定,也永远忘不了父亲痛苦狰狞的面孔。我不明白他俩明明是战友,为何要以这种方式化解恩仇?也不知道父亲明明不再把弟弟当回事,为何还以死相拼?不过我知道,他的国度里一定有一种我前所未见的情感,而且这原本可以说是一种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情感。
6
2017年,已是烟云弥漫的入秋时分,聚散离合总是猝不及防,谁曾料想我骤然归来。
阔别故乡多年,一路上的风景仍在我脑中打转,片片花生枝叶,丛丛豆叶向阳,山野间充满了收获的希望。林木掩映的乡村尽头,一帘黄花梗遮到了眼前。再望远处的深山,一丝一缕地藏进黑色的幕布里,又渐渐地退出色来,然后慢慢地向我靠拢,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秋风煞人,可我想起那个抱着双膝坐在草地上的女孩时,还是落下了眼泪。
从辽阔无边的厦门岛一下子步入家中,那种扑面而来的现实气味儿,依然能够把人活活给憋死,要不有一点理性,有时候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工作不开心可以换,学校不开心可以换,但家不同,你能轻而易举地换掉吗?不能。当我看见父亲和邻居在门前比划着十四年前的那场大战时,才惊讶他们并非生死对头。
这天,我给父亲带了进口烟,也带了许多特产。一想起从前,我会难受,一难受就越要展示这些东西的昂贵之处。末了,还故作谦虚地表示这不过是身为子女能做的一点小事而已。我知道他心底难受,我感受到了那种憋着眼泪的酸楚,可是从头至尾,他只是笑,笑的时候,眼睛睁得老大。我在等着,等那一滴泪落下来,一切才可能释然。我完全不需要在乎父亲的感受,也是这一刻起,我好似才知道他老了似的。
无风的傍晚,落了叶的树枝苦苦地僵立在云朵间,晚霞里是一片迷雾。你在黄昏里走失过吗?可一再承受贫穷和孤独冲击的灵魂,会在一杯酒之后吐露出全部真相。那一夜,我向父亲说起了电商大亨全体宿迁,房价上涨的故事,也说起了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的环境,还说了大数据时代下的隐私问题。试图传递给他一个讯号,活在世上没有永远瞒得住的事实。后来还说到了国外的高新科技,也有那里的月亮,他听完之后,不敢轻易抬头,甚至不敢触碰手机,生怕秘密被窃了去。
我笑说他当初生我、养我也挺累,现在到了看破红尘的年纪,就不要卖命挣钱了。父亲似笑非笑地点头,自然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三弟大学才毕业,将要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我还戏说三姊妹是三兄弟,那么他早进了黄土的冷笑话。事实上,我知道他生来就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好比他知道蜂窝煤已经被淘汰,还堆了一屋子的煤。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时也有如今这样的科技技术,家中老二是不是永远都不会与这个世界相见?一夜,我大胆地这样问他。父亲忽然像97年的那天黄昏,迅速地站起身,立在堂屋正中间,风姿依然不减当年,和我对视。半天没说一句话,到最后摇摇头,把懊悔倒进酒杯中,一饮而尽时,我终于看见那一滴泪了。
一曲壁钟响起的柔声,滴滴答答地在寂寥的空间里回响。
父亲的国,在我不懈努力的轮番轰炸下崩塌了。这一夜,我问他当年为什么打不过单手阳关,他说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该还就应该还了。
瑟缩在桌角的阴影忽然消失不见了,那是月光照进屋里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哪个退伍军人何尝不懂得责任和代价呢?度过摽梅之年的我为何还执迷不悟?我也终于知道了白城河的芦苇由来,那是父辈无处安放的记忆。
那夜月白,素衣漫漫,往事尽是铺天盖地的来。忽而想起那草坡,那个燃尽烟花的黄昏,那些个无需解答的秘密……一刹间,我连劝父亲看破红尘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打过仗,挨过饿,也受过穷,所以他永远都不可能看破红尘。只因那种为战争而活的心态,让他越挫越勇,而那种让他为子女而活的方式让他越陷越深。
怀念一束枯草吧,兴许能成全我对往昔的眷恋。
我一直以为自己曾走近了父亲的国,还窥测了他的秘密,一屑不顾之后,风雨无阻地活了好多年;也曾喜忧参半地走向黄昏,轻触过它的衣裳,那淡墨似的云彩显得自由而散漫,直到天黑。当飞雪样的叶蓉布满原野,我已无法想象它飞舞的形态。如今,沉坠在叶尖的泥土是不能洗净的结痂,那累累负担可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父亲的国原来是条由信念、情义、责任连成的风景线,这些很好的回忆从没让我在人生当中失去过信念。至于父亲的国,究竟有多大,我想,你不洞穿他的一生,那是决不可能知道的真相。
也是这一年,白城下了一场大雪,父亲的煤仓让全村可以像人一样活着。
全网知识馆hupandaxue.cn,星光不问赶路人!